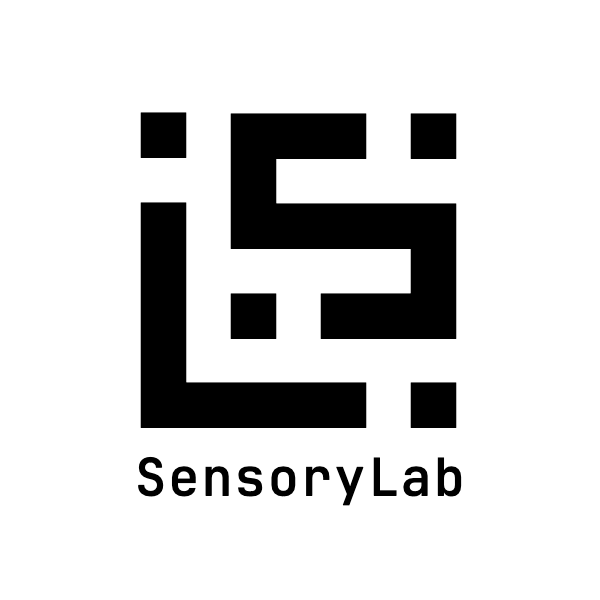Script:Screen Memory
━━━━━━━━━ 林欣怡
《藝術觀點ACT》67期,2016年7月出版

(人物進場時,因大雨滂沱而讓場景中的人物倉皇狼狽,驟雨讓群眾自動地往所有遮蔽物聚集,一列一排、一團一群。巴士從機場出發時原是烈日晴空,進入九龍卻開始因大雨看不清車窗外的景況。沒有布幕,沒有觀眾,場燈早已亮起,那位穿著棉襯衫牛仔褲的工作人員從巴士下站,事實上,上巴士時,她尚不知道該在哪一站下,她拿出預先抄好的地址,詢問旁座的港人。此行是為了採訪而來,她預先做了許多功課,行李箱裡躺著相關書籍,但腦中沒有具體安排。)
「妳住的那一區非常亂,夜晚外出時記得看好錢包。」這是出場的第一個陌生人物給出的局部口白,香港口音。車子行進,看著窗外深旺道的高聳大樓,「劇場不是考古學。」她想起皮蘭德婁(Luigi Pirandello)在〈義大利劇場導論〉裡的一句話。劇場不是考古學,句點、略號、「劇場是一種生活的舉動」、略號、「戲因此得以從這一瞬間進行到下一瞬間」、略號,巴士到達旺角站,句點。旅館房間在十七樓,非常的小,小到行李箱打開便沒有行走的地方,但乾淨,她翻開皮蘭德婁的《六個尋找作者的劇中人》(Six Characters in Search of an Author,1921)中譯本。
第一幕:舊鬼與新魂.尋找詞語的肉身
位置:旺角新興大廈(2016.05.28)

父親:(向前走到舞台表演區邊緣,其他人跟隨著)我們正在尋找一位作者。
(略)
繼女:….我們被遺棄(side-tracked)了。
父親:是,被遺棄了。原來構思醞釀我們的作者,為了某些理由,決定不寫完這個劇本。
(略)
湯米:對不起,你是不是戲劇教授帶著學生旅行做什麼奇怪的田野調查?我是說,你們究竟來這裡做什麼?
父親:我們要活起來。
導演:但劇本在哪裡?
父親:在我們身上,先生。
—皮蘭德婁,〈六個尋找作者的劇中人〉,1921
「我們要活起來。」一個被作者遺棄的角色要求,因為作者的遺棄,讓角色無法「存活」。「人會死,作家會死,但所有被創作出來的,將永遠存活。」。作為作者創生的「角色」,他指出自身的「真實性」,是不可被任何演員所化身的,這裡所謂的「真實性」,其實是「虛構的真實」。作者筆下的角色可以被無數個不同時代的演員演出、被無數個不同立場的編劇所改寫、被無數個不同風格的導演所定影,但角色只有一個,一個疊合了諸種版本靈魂的「原角」,亦即無論有多少個新魂,舊鬼只有一個,此唯一虛構的原角,便是其真實性所在,永遠威脅、質問著新魂的述行性(Performativity)。甚至可以說,新魂所有複雜的述行性來自於舊鬼真實性的威脅,兩者衝突辯證糾纏鬥爭,或者彼此對話擬仿。透過劇中劇的安排,皮蘭德婁辯證戲劇的虛實與本質,當被擱置的角色現身開口說話,他進行的不僅僅是「主客反轉」的共時劇碼,也是對「現實條件」進行清算檢視的直接要求。
關於「劇中劇」,或者更精確一點說,與這個專題有關的「劇中劇」,起始於閱讀鍾喬一九九四年出版,關於臺灣新劇運動者簡國賢的劇本《壁中壁》。根據鍾喬,《壁中壁》主要以藍博洲報導文學作品〈尋找劇作家簡國賢〉(下簡稱〈尋簡〉)改編而成,〈尋簡〉一九九〇年十月刊於〈自立早報〉「人間實錄」,後收錄於藍博洲有關五○年代白色恐怖的調查報告《幌馬車之歌》(1991)一書中,這些關於二二八事件的資料採集,為《人間》編輯部臺灣「民眾史」的企劃之一。鍾喬《壁中壁》以報告劇的形式,現時的視角,舞台空間時間的交錯,演員在劇中談論〈壁〉,也在劇中雙身演出簡國賢的〈壁〉。簡國賢在鍾喬另一個劇本《腳蹤》裡,化為「民賢」,其妻為「惠子」,當第五十八場景中保安司令部李上校對惠子宣告:「妳的匪諜丈夫已經被我們逮捕了…他逃亡了三年的戲落幕了。」時,這位仆倒在馬場町的劇作家新魂仍未散去,在一九九五年鍾喬小說《戲中壁》裡化為簡阿賢。藍博洲在《聯合文學》的〈關於〈壁〉的出土〉一文中描述了他尋找〈壁〉原作劇本的經過,先是找到簡國賢遺孀簡劉里女士,接著詢問當年飾演〈壁〉奸商一角的演員、以及可能有腳本的「美國仔」等人,皆未能讓〈壁〉重見天日,直到他再次拜訪簡劉里女士,她忽然記起仍保管著簡國賢的一些稿子,於是「日文、中文的手稿,以及宋非我編譯的、油印的閩南語腳本,還有一本簡國賢自己細心剪貼的有關〈壁〉的種種新聞報導與劇評」(藍博洲,1994:71),交到了藍博洲手上。而〈壁〉劇本,包括這篇尋文,於二〇〇六年一同刊錄在鍾喬所著的《簡國賢》一書中。劇本作為一種文學,它的政治性並非劇本中所有對角色描寫的「詞語」,並非「詞語」所描述的「內容」關乎政治,「而是透過命名、透過召喚、透過命令、透過謀劃、透過引誘,它們才割裂了實存之物的自然性…使他們相互分隔,結合為不同的共同體。」(Jacques Rancière,2004:3)作家在建構「詞語」文本時,在與過往的文本交涉時,在試圖將詞語投向現實時,這所有的調度便是詞語化成肉身之處。在那裏,新魂舊鬼的共臨重構彼此,這便是其政治,其政治即彼此共臨重構的諸身叢集,對現實提出再倫理化、再美學化、再政治化的引誘中。
第二幕:口號是劇本的一部份
位置:香港.石硤尾工廠大廈(2016.05.29)
人物:莫昭如

演員:請大家工友一齊來,一齊叫口號。我們要求最低工資!
(其他演員加入,手持標語,演變成遊行一樣。一名扮警察的演員出現,手持警棍,阻止行列繼續前進。)
警察:收聲、收聲,我叫你們收聲呀!嘿!搞事份子收聲啊!(搖動他的警棍)
演員:我們正在這裡演戲,話劇!
警察:演戲?(指著標語)你們在這裡叫口號手又拿著標語,立即停止!(略)
演員:…..我們全部是藝術工作者,民眾劇場的工作者。(略)
警察:為什麼要喊口號?停止,不可以喊口號!
演員:我們這個戲就是這樣。口號是劇本的一部份。
—莫昭如,〈薩夫達.哈許米在印度街頭的生與死〉,1994

莫昭如是在閱讀印度學者巴魯洽(Rustom Bharucha)〈給死者的一封信〉(Letter to the Dead)這篇文章時認識薩夫達(Safdar Hashmi )的,他引述「…你被人謀殺,被毒打而死。你頭部有多處傷口,不過死有全屍。你犯了什麼罪控制如此下場?只是演戲。不同的是你演戲的場地不是安全的Mandi House劇院…在這些地方,所有的抗議都被認可。但你演戲的那些地方是最籍籍無名的戰場和劇場——街頭。」(Rustom Bharucha, 1990:21)未久,莫昭如閱讀了荷蘭學者尤金(Eugene van Erven)的〈劇作、掌聲與子彈——薩夫達.哈許米的街頭劇〉(Plays, Applause, and Bullets. Safdar Hashmi’s Street Theatre,1988)文章,寫信給尤金,取得JAMAN劇團地址打算去新德里親自拜訪但未果,輾轉前往孟加拉看了薩夫達的劇《那識字的人》。之後,莫昭如在香港舉辦了一個紀念薩夫達的活動,邀請孟加拉民眾戲劇工作者拉釋(Mamunur Rashid)主持工作坊,於粉嶺的田心臨屋區等處演出薩夫達作品《機器》(Machine)和《口號》(Halla Bol)。我則是在閱讀莫昭如這一篇關於薩夫達的文章中動念前往香港尋找莫昭如。在作者節錄的《口號》劇本開場對白中,「我們這個戲就是這樣。口號是劇本的一部份。」這句話清楚地演示了美學政治的雙重性。作為劇本,「口號」必須透過演員的「使用語言」(日常性)來操作;作為語言,使用語言的「日常性」所可能引動的感知則因劇本的「美學性」而非日常化,成為「舞台調度的語言」。正是此種雙重性格,讓「口號」存活於美學現實中,一方面模仿現實,一方面挪移了現實。這也是為什麼巴魯洽會直言「在劇院這些地方,所有的抗議都被認可。」因為在劇院(美學場所)中,口號是對現實的模仿;但當薩夫達的口號在街頭演出時,不僅是模仿抗議自身,且模仿抗議自身就是現實,因為他透過拋擲美學語言、進入「日常空間」,要求現實感知的直接回應。
美國學者畢莎普(Claire Bishop)曾引述蘇珊.巴克摩爾斯(Susan Buck-Morss),「群眾劇場不只是把革命搬上舞台,它更上演如何將革命搬上舞台:表演有潛在的政治危險,因為它重現了革命顛覆的條件。」(Bishop,2012:60)一方面模仿現實,一方面挪移現實。畢莎普指出,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後的「無產階級文化運動」(Proletkult)試圖結合勞動(藝術家與工人合併—身份)、生活形態(家裡與工作場所—空間)及感知(革命意識—主體)的重新整配。從生活裡實踐,劇場化的生活讓每一分鐘都在劇場,換言之,每一分鐘都在進行革命、生產與創造。「空間」是社會建構的系統再現,透過生活形態的組配,我們可以判別此空間中個體的身份脈絡,對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而言,空間是知識系統轉為權力關係的場所。在這樣的系統下,日常生活的空間是割裂的、移動的、分離的、不連續的。是以,透過「土地—勞動力—資本」三位一體的整配,便是一種將空間(與空間中的身體)等級化、差異化、控制化的手段。「土地—勞動力—資本」事實上亦可與俄國無產階級文化運動中的「生活形態—勞動—感知」的三位一體進行概念上的對位。 當空間中的主體從日常性中剝離出來(如戲劇活動),便是從重複性的身體動作進入姿態化(gesticulate),姿態永遠是關乎文化而非自然的動作,這些姿態能給出空間異質性、進而重新雕塑空間,驅動形成個體極微化差異的能量。尋此視角,民眾劇場便是以「戲劇」作為溝通媒介,將話語、身體坐落於各種命題概念的坐標中,模仿現實、召喚現實、挪移現實,於各種割裂的日常空間中發動感知的解放。於是亞陶(Antonin Artaud)說:「要改變戲劇中話語的作用,就要以具體的、具空間意義的方式使用它。」(Artaud,1970:72)
* * *
「妳不先到處看看嗎?」莫昭如問我。
我愣了一下,隨即回應了這個開場白。莫昭如帶我到CCCD(社區文化發展中心)的輔導室、展覽廳、活動室等處介紹參觀,在沙鷗麗(Saori )紡織機前停下:「這個很有趣,是一個自由的手織藝術,一位日本藝術家創立的。」走出CCCD,他站在通道上指著石硤尾工廠大廈的中庭說,「香港在八〇年代時的工業很多去了中國,這裡後來改建為藝術村(art village),目前約有一百二十幾個單位。」這棟大廈在五、六〇年代原本是家庭式輕工業工廠(cottage industry,又稱山寨廠),裡面有好幾百個單位,二〇〇〇年時空置,後活化改建為藝術村,補助不同類型的藝術家、藝術團體空間租借,近來在低層加建一黑盒劇場供實驗性表演場地。莫昭如幾乎是一層層地帶我逐一瀏覽,每一個單位門口牆上仍保留著過去工廠的名稱如中華鞋廠、大專印務…,「我們在這裡八年了,是最早進駐的團體之一。」站在八樓外圍的通道上,他指著俯瞰的足球場,那裡有一群移工正圍圈圈做活動,眺望看去,眼前是一幢幢四十多層樓的公屋大廈,大廈旁較低的是舊公屋,石硤尾邨的大樓造型一致,規劃為美如樓、美映樓、美薈樓等。李俊峰曾提到,一九四九年後大量中國難民南逃,石硤尾聚集了一群群難民,因港政府沒有安置政策,難民自行在山邊蓋木屋而居,一九五三年聖誕節石硤尾發生大火,多個木屋區變成廢墟,五萬多災民無家可歸。 因為這場大火,港政府興建了29棟H型的徙置大廈,是香港第一代的公共房屋:「石硤尾徙置區」。石硤尾這一區,在一九五六年發生香港史上死亡人數最多的「雙十九龍暴動」,起因於南逃的難民中,亦有大批的國民黨政府人員,每年十月十日中華民國國慶都會在住處掛上大量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當年十月三日港政府下令禁止徙置區張貼旗幟或裝飾物,十月十日徙置事務處職員移除李鄭屋徙置區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與外牆大型的「雙十」徽牌,此舉觸發數百名群眾包圍辦事處,旋即發生暴動。檔案資料中,一張警方防暴隊與群眾對峙的照片為當時的H座(現為美荷樓),美荷樓就在距離石硤尾工廠大廈三百公尺處,這場暴動亦蔓延至旺角、油麻地等處。我想起與李俊峰前往CCCD的途中,經過美賢樓的小型社區廣場,有一群移工、老者聚在廣場跳舞,他笑言「這就是空間佔領啊!他們永遠能找到空間佔領。」。
回到CCCD,莫昭如從他的辦公桌某處翻出幾本書,以一本素面黑封、白色「藝術」兩字上疊著紅色「革命」兩字,名為《或者藝術,或者革命:莫昭如的藝術實戰》的書作為訪談的起手勢,一邊隨手翻閱,同時簡要介紹。畫面停在切.格瓦拉(Che Guevara)被軍隊槍殺之處的照片,「巴西、阿根廷、玻利維亞…,我們大概有十個人,去了這些地方,然後我們排了一個劇(《或者長毛,或者切古華拉》)。」他繼續翻閱,彷彿眼前的圖像文字與己無涉,接著,莫昭如輕笑兩聲,重重的將書闔上,轉身泡茶。今年六月七日,莫昭如將會與CCCD重演李俊峰、盧樂謙的《碧街事變》街頭劇,以些許不同的形式,在同一個地方演出,「現在還沒有劇本。」他說。
* * *

莫昭如(以下簡稱「莫」)──很多人問行為藝術(performance art)與戲劇有什麼不同?這要看你如何定義「表演」,理查.謝克納(Richard Schechner)的是一種,行為藝術是一種。
林欣怡(以下簡稱「林」)──無論是行為藝術、偶發或者劇場,是否有一種表演是沒有觀眾、觀眾成為概念本身?
莫──《熔爐時刻》(The Hour of the Furnaces,1968。由阿根廷導演索南納斯(Fernando E. Solanas)與赫提諾(Octavio Getino)所拍攝的紀錄片)這部片在阿根廷放映時,據說片子還沒放完,觀眾就去街道上示威、行動。放映與示威是不同的事件,但都可算是一種「演出」。
林──是,但並非所有電影都具備這樣的條件。
莫──高達或布萊希特一樣,強調某種「疏離」效果,目的是要求觀眾不要完全認同演員扮演的角色,而是要我們一邊觀看一邊思考。另一種看法是,觀看時除了身體的「進入」狀態,受到角色影響,也同時能跳開角色去思考,這兩者是可以同時發生的。演出時亦同,當觀眾進入表演時,我們與觀者保持疏離。
我認為行為藝術更為不同,它是非常有機且真實(truthful)的,表演者是把自己最真實的一面呈現在觀眾前,他要說一些話,要表達,他將自己放在台上,演出的就是自己。例如當他們要求觀眾去經驗痛苦時,便用刀割劃自己,或更激烈的方式。
林──而您選擇的是民眾劇場的方式。
莫──我是一個政治藝術家,透過藝術、戲劇的方式與群眾對話。最初就是在群眾中演出,接著以工作坊的方式讓每個人都可以做演出,試圖實踐社區民主,現在朝向的是民眾文化、社區文化。其實不只是戲劇,民眾可以透過音樂、舞蹈、繪畫等不同的方式去發聲。目前我們正在推廣喬治.馬凱(George McKay)的社區音樂(Community Music: A Handbook: Pete Moser and George McKay, eds., 2005),另外是二〇一五年的「區區音樂.彈唱香港」工作坊,讓民眾做自己的音樂。
林──這些社區藝術有沒有固定的方法?
莫──我們有很多不同的創作方法,社區音樂部分,過去我們都是邀請Pete Moser(英國社區音樂家)來指導工作坊,鼓勵民眾寫自己的歌。戲劇部分也是以不同的方法論進行,如奧古斯圖.波瓦(Augusto Boal)的方法是「受壓迫者劇場」(Theatre of the oppressed),而菲律賓教育劇場,則發展了自己的方法。另外「一人一故事劇場」(Playback Theatre)由強納森.弗斯(Jonathan Fox)和他太太所發展的方法,我們曾邀請他來香港舉行工作坊,這種方法很強調「公民演員」(citizen actor),多年前我們也曾經受邀去臺北、臺南做一人一故事劇場工作坊。這些工作方主要是透過各種方法讓民眾能夠自我表達,且並非是講者「教導」參與者如何行動,而是以互動、對話的形式完成。每一個參與者的內在都有一個金礦,工作方的意義就是讓這些內在都能夠表現出來。波瓦的方法技巧從簡單的遊戲開始,例如形象劇場(Image Theatre),用簡易的動作將自己的感受「雕塑」出來,因此能夠讓參與者很快地進入狀態,接著再操作比較深入的方法。
林──就我的理解,波瓦的「受壓迫者劇場」有一個方向,希望透過劇場方法啟動民眾的抵抗意識,您在香港操作社區劇場的經驗與觀察裡,是否有這樣的意識?
莫──民眾劇場的方法是任何人都可以操作的。這樣說好了,有人在香港組織一個小團體,去澳門賭場裡做論壇劇場(Forum Theatre),訓練學習如何處理各種顧客問題,他們辦論壇劇場賺了很多錢,因為方法很簡單,所以要看你用在什麼地方。
林──阿峰將街坊的口述轉譯為劇本演出,這樣的方法並非事件本身,而是以另一種藝術語言去直面歷史,您將在六月七日重演《碧街事變》街頭劇,您如何看這樣的「重演」?會以怎樣的角度處理「重演」歷史事件?過去您曾參與許多社會運動,創辦《70年代雙週刊》,作為一個無政府主義者,您觀看這些事件的角度是什麼?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讀到您提及街頭演出是「爭取直接控制表演空間,透過身體佔領上演反抗的美學」,能否就這些角度去談談?
莫──對我來說,藝術或者民眾劇場,都是朝向民主的一個方法。這不僅是操作工作坊、行為表演的經驗,而是「民主」的經驗。我希望每一個人都唱自己的歌,演自己的戲,這背後有一個想法。我們用八小時或九小時也好,讓原本是八、九小時的工作或睡眠,轉變成自身喜歡的勞動,讓群眾都有時間去參加藝術活動。因此你不再是一個被動的消費者,下班回家就看電視,而是一個主動去創作的主體。並且讓這種狀態成為每個人「回家吃飯」的狀態一樣,不再是到酒店、飯館、咖啡廳去消費,而是做自己的電視節目,自己的演出。這不僅是改變我們消費的行為,而是將整個社會的資源「重新分配」。這就是為什麼我要透過不同的工作坊,讓民眾自由參與;同時,每個人都回家吃飯。我不知道妳是否同意(回家吃飯),但這是一個很顛覆的想法。
林──回到日常的革命。
莫──是,就是這個。因此工作坊的方法很重要。

柯翰(Dan Baron Cohen)是一個詩人,受波瓦及其老師愛德華.邦德(Edward Bond,英國劇作家)、恩古吉(Ngugi Wa Thiong’o)的影響。柯翰曾批評波瓦,特別是他的論壇劇場的方法。波瓦的論壇劇場是站在受壓迫者、工人的立場,要求工人去解壓迫、去戰勝。柯翰認為這樣的方法不是「對話」,對他而言,「對話」這個方法很重要,他目前住在巴西進行「永續社區的生活教學」(pedagogies of life to sustainable communities)活動,《旱期之獲》(Harvest in Times of Drought)這一本書就是他操作「演/變」(Transformance)工作坊的內容。「Transformance」即Transformation performance、Performing for transformation的意思。這是一個長時間的工作坊,參與者透過不同的活動,去認識自己、自己的過去、父母、社區,然後認識自身的國家歷史。接著他們開始生產藝術計劃去進行改變,透過不同的藝術方式完成,這是我認為很好的方法。他們成為一種很具文化性的藝術社區,面對不同的問題都能夠給出自己的聲音。
我們在香港就是試圖將這些不同的方法帶出去。目前我們操作的「一人一故事劇場」,理想參與人數約五十人,參與者講真實的故事,其他演員將他講的故事當場即興演出,這個「演出」就是一個「禮物交換」,送給說故事的人。這也是民眾劇場,民眾自己的故事成為演出內容。論壇劇場則是透過一個「命題」,命題不僅是自身所關心的,也是眾人所關心的如土地問題,接著尋找檔案資料成為劇本演出,以此命題去追問民眾面對國家機器時可以做什麼?然後去個社區演出,論壇劇場需要長時間與機緣去操作。相對來說,「一人一故事劇場」比較容易。現在我們試圖將兩者結合成為「展望劇場」(Playforward Theatre)。例如參與者講述家暴事件,其他人將這個故事演出,這是「一人一故事劇場」的部分,但作為禮物,這並沒有進入如何解決、反抗的部分。是以我們加入「向前一步」(playforward),去探討如何用不同的方式去面對。
CCCD也有「表達藝術治療副修心理學碩士」(M.A. in Expressive Arts Therapy with a Minor in Psychology)的課程,提供藝術治療的訓練。這樣的想法起始於我之前談到的菲律賓教育劇場,他們的方法裡有一個「ATORS」,A=Artists、T=Teachers、O=Organisers、R=Researchers(藝術家、教師、組織者、研究員的集合),這是很好的方法,其中的「教師」並非上對下式的,我們也希望他是一個「好人」。我的意思是,這個人是對自己有要求的,不斷自我成長的個體。於是我思考怎樣的人符合這樣的想像?我認為藝術治療師、戲劇治療師、舞蹈治療師等可以提供這樣的方法,讓參與的人透過這樣的過程去認識自己,學習怎樣去跟人溝通。
林──紗鷗麗(Saori)手織藝術也是這些課程之一嗎?
莫──那是我多年前在另外一個機構工作時引進的,這幾年我們希望將紗鷗麗與其他工作方法結合。
林──過去到現在的您有何轉變?或者有什麼是不變的?
莫──過去我所做的我仍舊認同,我還是一樣,反對資本主義、反對極權的共產主義,我期望有一個沒有壓迫的社會。過去我參加示威遊行,現在以另一種方法(演出、民眾劇場等)去表達我的立場。我希望香港越來越多「ATORS」,不僅是「ATORS」,且是「好的ATORS」,關心自我成長,發展不同的方法。不僅是我們在做這些事,這裡(石硤尾工業大廈)有很多我們的同伴,包括李俊峰,都在做一樣的事。我們常說把左腳的腳趾放在右腳趾的前面,就前進了一步,雖然離目的地還是很遠,但我們仍舊往前了一步。
第三幕:被遮蔽的底片
位置:上海街香港上海街視藝空間(舊為活化廳)(2016.05.30)
人物:李俊峰、三木(陳式森)

父親:「我們正在尋找一位作家。」
繼女:「你們可以成為我們的劇。」
父親:「我們要活起來….經由你們。」
—皮蘭德婁,〈六個尋找作者的劇中人〉,1921
這場訪談起心動念於對「重演」的追索,訪談結束後,李俊峰帶我再次行走了《碧街事變》街頭劇當時的演出路徑,鏡頭一路從上海街、碧街、彌敦道再回到舊活化廳的檔案室。藝術家從箱子裡取出久未整理、關於六四、關於這場劇的相關資料,亦包括了一本本一九七〇年代,莫昭如、吳仲賢等人創辦的《70年代雙週刊》彩印版。我花了將近三小時蹲在地上逐一地翻閱拍攝那些資料,鏡頭至此,不再只是「重演」一個歷史事件,而是諸個歷史事件的回音同時敞開。檔案資料中,除了訪談提到的那張八九年關於大遊行的傳真,五年來活化廳舉辦關於六四事件的活動,碧街騷亂多年來的檔案收集,還有一張立在陳亂檔案架邊的照片。拍攝者為陳光,根據阿峰,陳光是八九年被安排做隨軍攝影的軍人,當時他拍攝了許多六四事件的現場照片,覆命時偷偷藏起其中三卷底片。這些被遮蔽了二十三年的底片,其中一張在二〇一二年於活化廳首度公開。這讓我想起成立「星光演劇研究會」張維賢之弟張才,在一九六〇年銷毀的二二八歷史現場拍攝的多卷底片。鐘喬在一九八八年十二月號《人間雜誌》的〈先行代攝影家—張才〉一文中對此描述:
「二二八事件發生的當天,我接獲朋友打來的電話,說是有人在圓環邊示威遊行。背起相機,我馬上趕赴現場,眼看人群越聚越多,我拿起相機拍下了一張張抑憤的臉孔,又跟著亢奮的口號,一路尾隨到公賣局…..」
他說,當時在示威的人群中也有人憤怒地指著鏡頭背後的他。「幾經解釋之後,他們才和緩下來,」記憶中,張老緊接著又以慣常淡漠的口吻說,「前些年,我把這些照片都燒掉了。」
「燒了!」
「嗯。」他說。
問他現在後不後悔,他簡潔地說不。(頁三六)
歷史現場的鏡頭,一種朝向受難者,記錄著眼前發生的一切苦痛、舉證歷歷;一種站在受難者的位置,鏡頭朝向壓迫者,利刃追蹤解剖,兩者交錯成對歷史的敞視、對事件的批判。事實上,這兩種鏡頭與報告劇、報導文學有著相同的路徑。今年四月中鐘喬製作、林靖傑導演的《幌馬車練習曲》報告劇座談中,差事劇團團員李哲宇以自身策劃關於六張犁白色恐怖亂葬崗的計劃《紅字團2014-1949》作為經驗參照,提出報告劇中演員以白布遮眼,如同白色恐怖時期的「遮蔽」。這一群已無口舌為自身辯解的歷史魂魄,被國家殺人後亂葬於六張犁「歷史現場」,卻在二〇一四年遭到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發文認定有「侵占國土」之嫌。此種空間意義隨時間遞嬗的政治荒謬,都是當下社會感知的集體遮蔽。面對遮蔽,「重演」(reenactment)不僅是進入歷史瞬間的現場,亦是重新創造身份、重新理解空間、重新分配關係的現場。「重演」的鏡頭,一邊如後照鏡朝向過去,掃描著曾被記錄的舉證歷歷;一邊將當下社會被遮蔽的感知,解剖重構。
畢莎普在分析埃夫雷諾夫(Nikolai Evreinov)歷史重現劇作《攻佔冬宮》(The Storming of Winter Palace,1920)時描述,群眾透過戲劇創造自身的歷史,當過去與此刻疊合,歷史事件將轉化為「臨在」的記憶。「歷史重現本身經過嚴謹的排演,旨在創造一個屏蔽記憶(screen memory),甚至勝過原始的事件,讓革命裡的次要事件在集體想像裡成為焦點,即使是對曾經參與原始事件的人亦復如是。」(Bishop, 2012:59)「屏蔽/銀幕/遮蔽記憶」在精神分析那裡,所陳述的事件是現實與當下情境滲入詮釋、想像交錯的故事,而非源始場景。主體透過與主事件相關的小事件的專注,不自覺地規避或壓抑自我對主事件的傷害性。在這樣的情況下,重點是主體如何「行動化」(acting out)事件?亦即,叩問如何主體「行動化」(滲入詮釋與想像)的記憶場景,對主體而言才是有意義的分析,而非固著追蹤在源始場景的真實性困境中。人類學者金斯伯格(Faye D. Ginsburg)在《媒體世界: 人類學的新領域》(Media Worlds: Anthropology on New Terrain,2002)一書中,則將「屏蔽記憶」作為一種能夠讓原住民將被遮蔽的歷史「恢復」、進行「自我陳述」的方法。然這並非易事,當「他者/研究者」透過「媒體」對「異文化/被攝者」進行拍攝研究時,要求的究竟是「文化本真」?還是將對象「當前」的身份自我陳述出來?拍攝的方法、交談的過程、詞語的轉譯、文化位置的分配,甚至最後檔案如何「觀看閱讀」,都是必須謹慎處理的路徑。對此,金斯伯格傾向於借由屏蔽記憶的方法,揭露對象當前的文化身份如何被遮蔽、如何被建構、如何被觀看的視角。透過前述三種論點,我們將屏蔽記憶的鏡頭轉向二〇一四年盧樂謙、李俊峰等人策劃的《碧街事變—六四滾動街頭劇場》。這一齣街頭劇並不試圖本真重現源始場景,亦非重演六四事件,而是聚焦在八九年六月七日凌晨,在油麻地發生的一場騷亂,如何讓香港人錯過為六四事件而全民罷工、罷市、罷課的大遊行行動。

* * *
林 ──六四事件對香港的重要性、延續性,相對於台灣來說,非常不同。你曾提到香港潘毅教授當時到北京參加五四遊行,偶然見證了六四事件,立即做了支援回應,另外香港的「支聯會」(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在事件發生時亦採取了行動。能不能談談香港當時面對此事件時的情狀?
李俊峰(以下簡稱「李」)──整體來說是很複雜的,當年它是一個集體行動,二十七年之後有些東西還在討論、變化。以前六四是一個symbol(象徵),它的關鍵詞是「記憶」,支聯會有一句話是「不敢回憶.未能忘記」。在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八日時,香港有一百五十萬人上街進行遊行支援這場民主運動,可以說,香港大多數人都在關注這件事,在人數比例上,參與很多。在那一代的人很多是第一次走上街頭。活化廳的街坊很多是第一次參與遊行,之後也沒有再上街頭;另外有些人隨著時間過去,每年仍堅持做一些事情去紀念六四。有些人受到很大的衝擊,有些人繼續生活,二十七年之後,有些人政治立場改變。關於這個事件,它的關鍵是立場與良知的問題,面對這樣巨大的不公義與國家暴力鎮壓時,主流的說法是我們要不停地去談、去行動與悼念,每年都會有(維園)燭光晚會去追憶,這也是世界上唯一公開且這麼多人去悼念六四的地方。 但我覺得還有很多面向沒有談清楚,如果只有談到記憶、傷痛、悲情的部分,六四就只能停留在那一代人。我是一九八四年出生的,六四時我五歲,那樣的年紀即使腦中有記憶,也很難聯繫到事件本身的重要性,都是一些很零碎的片段。以一個八〇後的角度去看,我想從兩個部分去談。一是六四事件應該專注於以什麼方法、什麼意義去傳承?以什麼說法?什麼論述去談去深化?另一個是六四跟香港的關係,這跟英統有關。它跟一般的國家暴力是不同的,與台灣的二二八事件、非洲大屠殺、猶太人屠殺等的國家暴力事件不同。八九民運(六四)關係著香港當時的前途,與香港政制主體的出現。香港過去是英國殖民地,八九民運影響到九七回歸之後,香港的政治處境。學生當時提出的反貪污、開放民主、重評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等訴求,香港人是非常認同的。當時學生提出訴求時被北京政府鎮壓,並被指為別有用心、背後有人指使操作。北京政府越是打壓,香港人越支持學生。而當時支持的群眾包括了知識份子、社會精英或一般民眾,都想為八九民運做些什麼。活化廳街坊曾告訴我,過去這裡是紅燈區,當時曾有性工作者自發地組織遊行聲援,在八九年那樣保守的社會氛圍下,這樣的自發性遊行並不常見。因此可以想像當時香港各階層的民眾皆以自己能力所及的方式進行支援行動,都想透過行動來發聲。這反映了香港人在面對壓制時,所做的價值選擇,接著形成「運動」。我認為,這才是所謂的「記憶」。
「記憶」有很多版本,可能也未必是真的。我在做《碧街事變》的口述資料街頭採訪時,問到了很多其他的事情。碧街(油麻地)在一九八九年、一九八十年、一九六十年都曾發生過大型暴動,這些事件因為時間的關係,記憶交錯,有些人的口述會事件交疊、不準確。但這些都不重要,因為「記憶」裡面有「故事」,而「故事」裡面有信念、有價值,這些才是重要的。這些故事好像都發生在八九年這個時空,如碎片一樣散落在各個不同的地方,香港政府、官方的檔案中沒有提到這些故事,支聯會也有他們的版本;而半官方如香港藝術發展局所支持的一些刊物,過去有些藝術家會提,但現在卻越來越敏感。因此在公共媒體裡,這事件一直不斷地收縮、不說。因此這些散落的故事怎樣收集起來,成為跟香港人有關的版本,怎樣聚焦在八九運動的精神?怎樣去談我們現在的處境?過去中國政府面對不同聲音的打壓如何聯繫到我們現在的處境?如何聯繫到香港現在的普選、收地、大白象工程…貧富懸殊等社會現況?重提這些故事是邀請大家去思考討論。
林──旺角、油麻地,包括我們昨天去的石硤尾,都曾發生過不止一次的暴動。在一九五六年時,這一年亦是台灣白色恐怖發生的時期,石硤尾居民因懸掛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而發生的雙十九龍暴動,據說是香港有史以來傷亡最嚴重的暴動。石硤尾暴動、六七暴動(六七左派工會暴動,Hong Kong 1967 Leftist riots)在旺角、油麻地這裡也有相關事件發生。你在這裡也據守了一段時間,你怎麼看這樣一個特殊的地方?這裡此刻有怎樣的特質?
李──對,當時三百多人包圍油麻地警察局丟石頭,準備攻陷。這個地區有工聯工會,在當時跟共產黨有聯繫,所以上海街這些地方常會發動暴動事件。
當時石硤尾居民掛中華民國國旗其實是有國民黨支持的,掛旗子便有一些錢可拿,會有人來清點,家裡有掛旗子便會給錢。石硤尾當時有很多的移民,對英國政府來說,他們需要的是一個港口作為轉運,他們只需要籠絡一小撮人、精英份子做生意往來即可,並不理會民眾生活的窮苦。因此當時香港民眾在這樣的情況下,自力更生的社群意識是很強的,自我與社區的強力連結是香港人很重要的mentality(思想情狀),但這部分一直沒有清楚的論述。而六七暴動正值文革,文革則呼應了反殖民意識,所以生活在香港(例如龍應台曾寫到的調景嶺)但同時跟共產黨、國民黨有政治聯繫的人,或者地下共產黨、地下國民黨(反共意識),或者只是逃難來香港的庶民、外國人等,都在文革時期反英、反殖等意識下,在香港複雜的特殊情況下演變至發起暴動。當時香港有人攻擊警察局,有人到處放炸彈,政府無法可管,整個社會是癱瘓的。最後是北京中央周恩來要求先留住香港,暴動才停止,不是英國政府停止的。正是因為六七暴動,英政府才意識到他們無力管制香港,因為會影響到經濟與權力運作,而對香港開始了新的政策。一方面進行社會福利,如公共房屋的興建,在此之前並沒有給香港難民這樣的社福或公民教育等政策。那個時期由港督麥理浩(Murray MacLehose)管理,我們稱為「麥理浩時代」(MacLehose Years),像是社會從暴動中甦醒一般。另一方面是「監控」,即開始進行文化政策,過去英殖時香港沒有做文化政策,相反的當時共產黨做得很好,因此年輕人一受到鼓動就會參與暴動。莫昭如就是那時期的年輕人,他當時留學回來時,發現香港有很多青年中心、活動等場所可以去,還有一九六九年開始舉辦的香港節(Hong Kong Festival)、清潔香港運動、公民意識等的出現。
關於油麻地(九龍地區),香港島跟九龍的規劃是不同的,九龍地區的規劃比較沒有那麼嚴密。英國政府的規劃都集中在中環(香港島),把整個中環、維多利亞山一路到海邊都規劃成維多利亞城,這是一種中心權力的結構,外圍的都不管。而作為外圍的九龍這邊每一次發生暴動,都演變成大事件,是因為這裡的街道住宅規劃比較不嚴密,不容易監控,所以政府非常怕九龍會發生暴亂,因為每一次發生都會很快地擴散。舉例而言,所有遊行都是在香港島發生,其中一個原因是政府總部、行政中心在那裡,就如台灣的總統府區塊。香港島的住屋都是高樓大廈,事件一旦發生很難蔓延,雖然平常那裡是生活區,但是政治上、空間上的規劃是把無法控制的聲音、多元的雜音都集中在一起控制。而九龍最大(也是香港最長)的道路叫彌敦道(Nathan Road),兩邊都是民宅、商店,一旦發生騷亂,會很快速的跟臨近的居民錯接連結,街道的形式也是,彌敦道很大很長,它可以很快地聚集很多人,驅散也很快。因此香港警察處理騷亂的話,在香港島是比較容易的,人民很容易可以集中在一點,附近的公路結構沒有可以藏躲的空間,可以很迅速的包圍、驅散群眾。九龍則不同,你可以到這裡補給物資,然後再迅速的移動,是一種網絡化的狀態。雨傘運動時,在旺角與在金鐘佔領的狀態就是不同的,這就是因為地理、空間與地方的特殊文化有關。旺角非常複雜,黑社會、中產、各種年齡層任何階級都有。就我自己而言,我一年至多去中環五六次,中環是中上階層的活動地區,物價較高。
林──若是如此,為何雨傘運動不先選擇在旺角這裡發生?
李──雨傘運動原本叫做「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和平佔中),由幾位知識份子、教授(戴耀廷、陳健民等)發起。透過聚集一定數量的人佔領中環主要交通要道,癱瘓其中一個點,讓中環無法運作。例如癱瘓了一間中國銀行,那麼中環地區的金融中心就會因骨牌效應而無法運作,這會影響到香港的金融,因為香港、北京、美國、北韓等世界各地很多金融流通運作都集中在中環,這就是他們的策略。而雨傘運動則是另一個偶發性的事件,由學生黃之鋒帶領,原定於十月一日發生,但卻在九月二十五、六日時,黃之鋒他們就佔領香港政府總部外面的公民廣場,但公民廣場雖是「公民廣場」卻由政府管理,不允許佔領,於是群眾就聚集在政府總部旁的金鐘聲援他們。當時警方進行包圍,同時準備催淚彈,在九月二十八日施放,這引來更多人自發性的聲援,但時間上與原定規劃不同,因此算是偶發性的運動。旺角、銅鑼灣這裡也是,尖沙咀則發生幾日就散了,但都是一種民眾自發的能量。
林──剛剛提到的幾場暴動事件,都有明確的政治性訴求,但旺角在今年二月發生的騷亂(魚蛋革命)則比較看不出這樣的傾向,這件事的發生是否是雨傘運動的某種延續?
李──年初的旺角騷亂其實也有政治性,活化廳在此時亦關注基層的小販,當時我們有一些朋友有過去協助捍衛小販擺賣的權利。雨傘運動之後「本土民主前線」(Hong Kong Indigenous)團體成立,以年輕人為主幹,主張本土、港獨等意識。他們當時把小販、警察、小販管理等的政策矛盾處提訴出來。事件發生時警察以他們的角度去處理小販問題,民眾以較激烈的方式去回應,漸漸地成為肢體衝突與更大的反抗,原初只有幾十人,後來民眾聚集去支援小販,要求小販亦有生存權。八九年的碧街騷亂也是短時間內所發生的暴動,但它同時俱有某種轉捩點的歷史性,如果當時碧街騷亂沒有發生,整個六四運動可能會往另一個方向走,香港的民主運動也可能會朝另一個方向前進,但我們不知道會往哪裡去。因此我稱那場暴動為「事變」,正是因為它這樣的性格。
林──《碧街事變》街頭劇如何開始?怎樣發生?
李──最初是由我和另一位藝術家盧樂謙一起發起的。其實活化廳每年都會為六四事件做一些什麼,而油麻地八九年的碧街騷亂這件事正發生在活化廳附近,我們覺得跟這裡的地區意識很有關係。我自己一直有一個社區行動的想法,而六四能夠喚起社區的共同討論,透過六四去聯繫社群,為這件事一起往前一步步行動。也是因為活化廳這個平台,它可以給出一個討論的聚點,讓關心這件事但尚未行動的人有一個行動的可能;或一些被主流媒體壓抑而無法言說的人,可以有言說的機會,這是最初的想法。

我想把這些故事都聚集起來成為resource(資源),一種可以累積的東西,不再那麼容易的被摧毀消散。活化廳正是這樣的空間在這樣的一個點上,把這些散落的故事收集整理成為檔案,把故事裡的情感信念都累積起來。活化廳當時已經談六四事件五年了,每一年我們都是用campaign festival(活動)的方式處理,因此我跟盧樂謙說這次我們只處理「記憶」這件事。活化廳在二〇一〇年,第一年做六四,就做了六十四件事去回應,包括展覽、行為、放映、來往廣場的單車行動等,兩個星期完成這些活動,但很難聚焦。因此這次《碧街事變》就是深入研究碧街騷亂個主題。這在過去並不常見,因為活化廳是一個容納許多聲音的平台,讓各種聲音發生的空間,也因此比較難聚焦。當我想以這樣單一深入的方法處理時,盧樂謙就提出了街頭劇的形式。雖然我跟他都沒有操作劇場的經驗,但是他在灣仔藍屋那裡曾看過類似的社區計劃,因此想以街頭劇去操作看看。《碧街事變》很多執行方法都是由他提出的,例如他建議街坊一起用木工建構街頭劇的道具。我則收集採訪街坊的口述記憶。接著在臉書發佈我們將做這樣的劇場消息,召集朋友一起開會討論,讓不同的人提供想法經驗參與這個計劃,有些人想採訪,有些人想做道具,有些人想演出…,於是開了一個工作坊。活化廳已有很多檔案資料,關於碧街的資料可能是收集最完整的,報紙、影片等,包括去年發現的一張當年的傳真。那張傳真是騷亂發生之後的隔天早晨,在支聯會還沒發佈取消大遊行消息之前所收到,到處在發的傳真。上面寫著「昨天晚上在旺角發生騷亂,發現發起騷亂的知識份子不是香港人,都是大陸派來的,因此大家明天遊行要特別小心」之類的文字。發現這張傳真時大家都很驚訝。
《碧街事變》的工作團隊都很年輕,很多都是八〇後,有三、四個女生是九〇後,他們看到資料都很驚訝,因為事件描述的催淚彈等場景就在活化廳旁,在當時事件這麼嚴重但我們卻都不清楚整件事。接著我們分頭去收集資料,盧樂謙在油麻地隨意地走訪一些人如水果販、果欄(水果批發市場)的工人等。其中德昌里一個曾經是黑社會的人說,當時如果購買黑社會的黑布條綁在手臂上,騷亂時就不會被挨打,這部分我們不確定究竟是不是真的,也沒有方法去證實。我們也去訪問了朋友陳景輝(社運人士),他亦關注碧街騷亂很久了;甚至附近麻將館的經理(黑社會)也走訪了,當時他下班後到活化廳口述他目睹的經過,畫面、聲音、他看到的景象,以及他對這件事的看法,甚至是非常個人的事情。事件發生時他正在麻將館工作,街道上有人在丟東西,下班時搭巴士回家就看到事件場景,有人從樓上丟東西下來、群眾一起叫囂之類的。我們收集了大約三十個這類的口述,包括沒有目睹事件的人。例如附近茶餐廳的老闆,當時他在茶餐廳工作,還沒將餐廳頂下來;作為員工,他在餐廳裡放了一個捐獻箱,讓客人可以捐錢給(六四)學生;老闆娘則記得騷亂,我問她有沒有因為這件事而造成的長遠影響?她的回答讓我非常驚訝,她說因為六四她才決定生孩子,她覺得要生孩子來進行反抗。她的兒子我們認識,在英國讀電影,也是比較左翼的。還有一些hidden story(隱藏的故事),茶餐廳老闆可以頂下餐廳是因為八、九〇年代很多人移民,他們對中國感到沒有希望,那一批有能力的人、一些知識份子等都移民到澳洲、加拿大等,因此有很多房子賣掉,因此老闆才可以頂下餐廳。另外一間茶餐廳老闆也是因為六四跑去台灣,之後再回來香港。平常去這些餐廳都不知道有這麼多故事在裡面,都是一些碎片,但包藏了很多的能量在裡頭。
林──收集完這些口述後劇本如何形成?
李──前後公開開了六次會,大家一起討論,然後決定用老中青三條線來談這件事,重演騷亂,盧樂謙建議以滾動、移動、非定點的方式重演。從碧街開始,到碧街的另一點(油麻地地鐵站),經過彌敦道,接著到上海街旁邊的公園結束。《碧街事變》是三個人的故事,因為騷亂而交疊在一起,第三幕則是二十五年之後他們回憶二十五年前發生了什麼事情。劇本部分,有一個成員想要寫一位老左的故事,他希望由雄仔叔叔演出,就由他來負責這一條主線,我則做一些增補。最後發生就完全是很機動性的,劇本尚未寫好,路線也剛決定,大家走一圈就開始,大家都戰戰兢兢的,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但是出來的效果比我們預期的更有能量。
林──演出後有後續反應嗎?
李──《碧街事變》並不是直接聯繫到這個社區的劇,它的定位是一個事件的reenactment(重演),我和盧樂謙是以這個事件的概念、行為出發,而不是以意識形態或理論去要求居民要參與。演出時有居民在旁觀看,但是居民知道我們在做什麼,我們也安排一些helper去解釋或發傳單,說明二十五年前在碧街發生了這件事,我們正在這裡重演。莫昭如跟我演出時的那個版本有直接跟街坊進行互動,例如直接現場詢問街坊二十五年前不遠處的那間小學如何如何等行為。《碧街事變》的第一個版本(DVD收錄)比較沒有這樣的互動,我想互動是發生在我們去跟居民採訪進行口述的時候,他們因為採訪也重新提取了他們的記憶,對我們也是一種提醒。對我和盧樂謙而言,我們都有很大的感觸是,曾經香港有一個面貌,到處都是自發去為它所肯定的自由民主平等、說不出的一種價值所付出過,這都是一種衝擊或承諾。隨著時間的過去,這樣的心情已經被沖淡,但這些被沖淡的歷史透過《碧街事變》,我們重新聯繫上了。
林──當時你以何種形式參與六四?
三木(以下簡稱「三」)──事情發生時我在東京,我是一九八七年九月去的。一開始我沒想到會這麼大,北京的朋友也跟我說現在情況懶懶散散,估計待不長,廣場上的人也越來越少。到了五月二十一日,突然就宣布戒嚴令,李鵬一宣布戒嚴令,就又鬧起來了。若是他不宣布戒嚴,把這件事定性為「動亂」,這個事情估計也就會疲累,群眾運動是很難預料的。我是在東京的朋友家裡看到報紙的戒嚴令。星期日開始,一些朋友很生氣,一些朋友卻高興起來。遊行當時,學生會給警察報的人數是五千人,後來是五萬多人,這很厲害。這遊行過了以後我們又以為不行了,結果到六月三日後,又起來了。那時候六月四日是星期日大家都在休息,忽然間,在日本的留學生有十萬人出來遊行。後來我就組織了一些同學,做了一個小的民運團體。吾爾開希他們逃出來後到了巴黎,成立了「民陣」,統合海外民運要大家加入,我們沒經驗也無所謂,就加入了,做了日本的分部「民陣」的籌委。進去之後就覺得這些事不是我做的,把選舉、章程看得很重要,這當然重要,但是他們沒有搞清楚一點就是,民主是一種生活態度、生活的狀態,而不是一個「制度」,民主制度只是其中一個部分。後來我就離開了,但我每年六四還是做作品,一直到現在沒有中斷。
林──你參與了《碧街事變》演出一角,怎麼看這齣街頭劇?
三──很好,這很在地。就在我們身邊發生的事情,我們居然不知道。而且這件事非常合理地不合理,那些人的出現、整個新聞報導的事態、檔案在何處?人被抓了之後如何了?放了還是仍關著,誰都不知道,這很奇怪非常不合理,但是「非常合理」。我相信這種不合理是存在的。前幾日烏魯木齊暴動時,我的朋友在新疆藝術學院,他們說七點半時在市區有暴亂,他在八點前後時看到黑煙,過一會他聽朋友說有大批的武警部隊的軍車進入自治區(新疆的政府)大院。但是鎮壓是晚上十點開始,武警給了一大段時間給所謂的「暴徒」去打、砸、搶。他目擊的情況是,他住的地方外牆發生打劫,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對街有些車子停下來,車子都是同一個牌子,服裝相似,拿的鐵棍是統一新的,一看就是訓練有素,有指揮者、有斷後的人,突然把市民都攔住,做了一些搶劫行動,這叫做「別動隊」(特別行動隊,擾亂人心作為鎮壓的藉口)。因此年初發生的旺角騷亂與八九年的碧街事件,我認為是別動隊操作的,香港市民不可能。你看香港市民這麼乖,八九年說不上街就不上街了。所以碧街這齣戲在排的時候我就在思考這些事,我們「錯失」了什麼?司徒華當時做了那樣的決定可能是保護自己,可能是保護支聯會,他必須下這個決定。問題是香港市民是一個主體,已經被激怒了,準備好罷市、罷工、罷課上街遊行,但因為某組織宣布取消,行動就取消了。這不是他的問題,是你的問題。正是這齣戲讓我想到這些事。
李──我有一個不同的看法。當時的香港人是第一次參與大型的運動,沒有什麼社運的經驗,因此當時不行動是有某種可以體諒的理由,重要的是有沒有從過去歷史得到教訓,這件事若發生在現在,我們會怎樣反應?八九年的碧街騷亂若沒有發生,是不是就代表香港整個民主有所推展?「錯過」是否是一個行動,意味著我們心態上、思考上還沒預備好所以錯過了?
林──你們都以你們的方式、藝術手段回應了這些事件,對你們而言,藝術的位置是什麼?
三──藝術是在要求創作者自己的內化,例如我們將要進行的六四漫畫展,其中一個漫畫家說:「這些人叫我們不要去悼念六四,我不知道要說什麼好,算他對。但這件事對我來說已經內化了,成為我的癌症,我怎麼把它拿出來?我已經沒辦法拿出來。」藝術是內化的,它不像政治社會運動那樣具體的發生一些作用,當它必須要發生作用時,就是政治有問題的時候,才會讓藝術現身。
李──我做活化廳也是在思考這些問題。先不去談藝術或非藝術、非學或非美學的問題,在香港這個政治脈絡下,你有自由表達的空間,與外界連結建立關係,這不是一種大型的社會改變。雨傘運動這種去中心化,或者是否要衝進立法院、支不支持港獨這些情況是政治把握了主要發言權,民眾自身表達的權利正一步步地收縮,從公共媒體到變成最後只能在自己身體裡面談。我們是否可以在一個很多元、去中心化的狀態下很自由的去表達?藝術與美學則是建立這種關係的工具、方法或表達方式。關於內化,《碧街事變》街頭劇發生時正涉及到參與者每個人對這事件的內在echo(回音),我會放在這個脈絡下去思考藝術的位置。
社會改變從來不是一觸即發的,問題並不是一個小販受到打壓,然後有人很勇敢地去聲援這麼簡單,而是社會是一個網絡,政治權力亦佈滿其中,而他們的能量能反過來包覆,民間組織、社會組織等在小販被抓了之後發揮了影響力。因此重點是我們在這些網絡發生事件時如何成為可以影響的其中一個點?我們可以建立什麼?建立的同時是不是在抵抗什麼?如果僅是自由表達,仍舊是中性的行為。必須要再追問多一點,更清楚一點。雨傘運動正是這樣的問題,已經有人出來了,但為什麼還是沒有改變?是歷史條件嗎?還是政治因素?距離下一場佔領有很長的時間,但我們有沒有預備好去做?這跟《碧街事變》街頭劇有關,就是去追問我們究竟錯過了什麼?如果支聯會完成一百五十萬人的大遊行,如果支聯會把握了更多的權力,民主派成為香港很大的一個反對黨,我們是否當時就朝向這個方向前進了?當時這些自主自發的能量我們有沒有看到?而這樣的能量又能朝向哪裡?
其實「本土民主前線」在今年年初之前也在旺角做過同樣的事情,試圖進行騷亂但卻沒有成功,這是有原因的。粗淺來說,一方面是因為社會情緒,雨傘運動過後大家更不相信很多事;另一方面主張暴力跟主張非暴力抗爭的兩條路線,在雨傘運動裡以非暴力路線為主,但運動失敗後這樣的主張正在崩潰,因此對我來說今年初的旺角騷亂其實是某種symbol。作為一個藝術家,我想的便是藝術或者美學是否可以再建立起一種討論的空間,那才是藝術跟生活、社會產生聯繫的時刻,藝術是最個人的,但當它聯繫到外界時,也是最政治的。
後記:在搭機返台等候登機時,收到阿峰一封關於當日討論的信件,實錄於後,以為補述。
六四其實像是一個處於傷痛、正義、權力、情感…等等眾多情緒與價值的交集之間,既深入到最不能言喻的個人感受,也交錯於香港這地方的歷史轉捩點,及至其獨特的文化身分。藝術在裡面其實一直扮演重要角色,既是抒發情感的出口(無論是傷痛、憤怒),也是讓當中價值與理念得以在歷史中流傳的重要介質。但因著國家政治壓抑的外在因素,這些實踐似乎將繼續處於邊緣…。所以,悼念與重提六四,其實也是說,面對高牆的每個人,如何找尋一個位置去反抗?重新言說那被壓抑的故事?
就「碧街事變」這事,我們當初的出發點是希望追尋背後的「真相」,然而這事後來倒反過來問我們:「香港人究竟『錯過』了什麼?」那場因騷動而錯過的行動,只是歷史的其中一個點,認清「錯過」什麼,其實就是辯明,我們能把握我抵抗的是什麼?其意義為何?
這種來自國家體制的暴力與不義,其實不會因一次半次的行動而被消滅,它或以另一面目再臨到我們身邊,或是警權的擴張、財團的收地、無可抵擋的官商勾結大白象工程…。
那麼「反抗」是否仍然可能?應如何實踐?是遊行示威?還是我們需要一些根本價值與想法上的改變?悼念、重提的過程,其實又在建立什麼?還是只僵化地每年在晚會上點點燭光?八九民運若指向一個理想,那其實是什麼圖像?是二十五年後雨傘運動裡的追求?還是在街上向這政權丟石頭?又或是日常生活裡的種種不妥協?不同於沈鬱於傷痛,我們想在這計劃找到希望的出口。
回溯碧街,同時我們也追溯到當年的香港人一片自主、自發的行動、連結,而這在今天的時空,很多人開始對那些「傳統」的代言體制(如支聯會)產生失望與質疑,那否定和解構以外,過去的故事卻留下我們一個問題:從民眾由下而上,多元卻紛異的處境下,基於平等溝通,聆聽差異,走在一起連結與行動的可能性又可以是什麼?
──李俊峰,二○一六年五月二十九日
第四幕:不是要一個答案
位置:美荷樓.石硤尾邨41座(2016.05.31)
在離開的前一晚,我在旅館看著由高登(Richard Gordon)導演、卡瑪(Carma Hinton)製片長達三小時的《天安門》(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1995)紀錄片,當影片播至柴玲接受美國記者金培力(Philip Cunningham)具爭議性的錄影片段( 1989年5月28日)時,重複倒帶幾次後我暫停影片,開始搜索此訪談的完整內容。這些爭議片段,在《天安門》紀錄片網站(http://www.tsquare.tv/)中有公開的檢索說明,其中亦包括柴玲、封從德致紀錄片製導的公開信(日期分別為2009年5月28日與2009年6月15日),以及片方對公開信的說明回應。針對片方多年來的不做修改,封從德持續地發表一些文章提出關於《天安門》紀錄片中因蒙太奇剪輯而造成的「敘事」、「用詞語翻譯」、「轉述與自述」、「形象塑造」等背離歷史真實與時序的問題,這些文章檔案等皆收錄於「六四檔案」網站(http://64memo.com/)中。
因為蒙太奇,某些感知被遮蔽了,事件本身不斷地質疑威脅著它的副本,正是因為事件對副本的扣問,這些紀錄片之外的檔案不斷地運動繁生著。記錄影像背負著某種原罪,某種因介質不同就不再是事件本身的原罪,即便鏡頭在現場,證人在現場,但「敘事結構」一旦進入,便朝著諸種相異的場景敞開對質。我們是否可以說,場外調度試圖運動的所在,便是事件與副本之間的那個「距離」,透過對「距離」不斷的去蔽、再行走、再觀看、再發生,同時調度可述者、可見者來消除我們對事件「被動地觀看」的位置,將我們從固定意識中驅逐,至少可以從某種形象塑造的官方歷史中自我驅趕至他者敘事中。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在〈被解放的觀眾〉(The Emancipated Spectator)中論及,「戲劇是一種共同體(community)的美學構造形式—即共同體的感知構造:共同體作為佔領(occupying)時間和空間的一種方式,作為一系列生活姿勢和態度,它們早於任何政治形式和機構[…]轉變人類經驗的感知形式。」(Jacques Rancière, 2009:6)從尋找詞語的肉身開始,歷史事件中的新魂舊鬼共時發出「我們要活起來….經由你們。」的刺耳聲響,舞台語言的調度、戲劇與現實的疊合、日常碎裂空間的佔奪、重複重演事件的自我陳述….,詞語道成肉身,這場場外調度或許只是讓我的身體行動能成轉譯為一個陳述一個故事的簡單要求:他種劇本的寫就。
離港這一日我重回石硤尾,根據歷史照片中的景象,拍攝已改建為青年旅社的美荷樓。接著回到旅館,請旅館老闆談談八九年離這不遠處的碧街與六四事件,「這個我不能幫妳,這關於政治,太敏感了。」停頓了一會兒,他接著說:「政府沒有錯,學生太胡鬧了。他們說要『對話』,『對話』什麼?」聽著這段預料中的話,我關掉攝影機,轉身下樓往巴士站前進。關於這七十二小時的一切,政治如何正確?影像如何得雪?我沒有答案。來香港本來就不是要一個答案。
皮蘭德婁著,羅博.布魯斯丁改編,陳玲玲譯,六個尋找作者的劇中人,1998,臺北市:臺灣商務
鍾喬,簡國賢,2006,行政院文化部
鍾喬,亞洲的吶喊—民眾劇場,1994,書林出版
莫昭如、林寶元編著,民眾劇場與草根民主,1994,唐山出版社
Pirandello Luigi. ( 1998) Six Characters in Search of an Author (Plays for Performance) , Adapter by Robert Brustein, Ivan R. Dee
Jacques Rancière. ( 2004) The Flesh of Words: The Politics of Writing, Translated by Charlotte Mandell,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 edition
Antonin Artaud. (1997) Translated by Mary Caroline Richards, The Theater and Its Double, Grove Press
Henri Lefebvre.(1995)Introduction to modernity, Translated by John Moore, New York:Verso.
Henri Lefebvre.(1987)The Everyday and Everydayness, Translated by Christine Levich. Yale French Studies 73(1987). Originally “Quotidien et Quotidienneté” in Encyclopedia Universalis.
Henri Lefebvre.(1974)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USA: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Henri Lefèbvre.(2004)Rhythmanalysis: Space, time and everyday life, Translated by Stuart Elden, Gerald Moore, New York:Continuum Publishing.
Rustom Bharucha. ( 1990 ) Letter to the Dead, Theater Winter/Spring
Claire Bishop. (2012) Artificial Hells: Participatory Art and the Politics of Spectatorship,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Jacques Rancière. ( 2009 ) The Emancipated Spectator, Translated by Gregory Elliott, London: Vers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