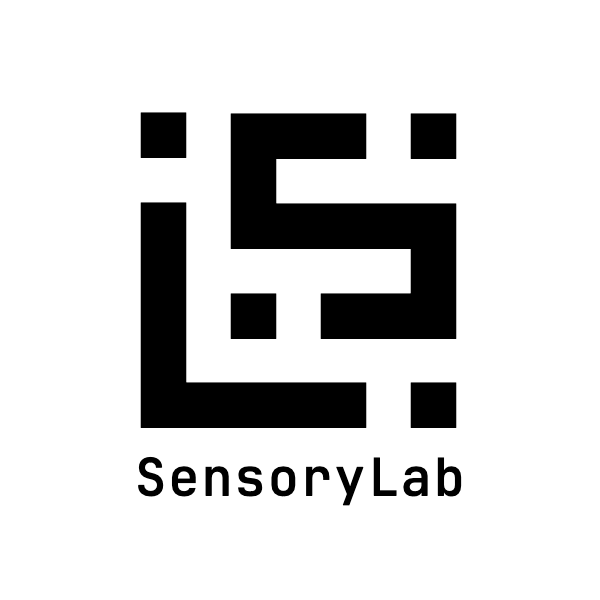Voice-Over of History,
Negative Theatre
━━━━━━━━━ 林欣怡,《藝術觀點ACT》65期,2016年1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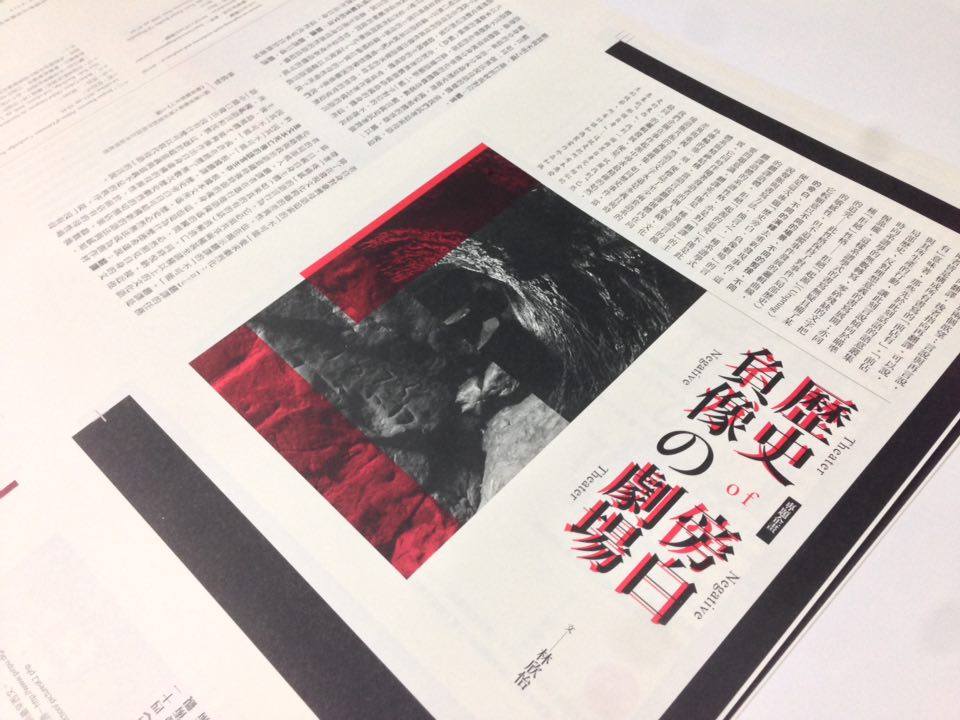
我們假定一個提問:當代藝術的主體技藝如何陳述歷史語脈中駁雜的個人存語?影像語法、歷史文本、個人話語,當翻譯成為一種主體技藝的述行(performativity),而語言成為連結混雜多語性的物質時,這樣的主體以何種樣貌被生產?要回答這樣的提問,必須先肯認翻譯語體的偶然與曖昧性格,用酒井直樹(Naoki Sakai)的話說,翻譯者面對的不只是多重的語言,且是語言的多重性。譯體自身的多重性(無論是地理、身份或內在的多重),如同不斷抹除、再書寫的演現實踐,可以說,這樣的演現所駐足的言說場所,其歷史性是流動的,它並不試圖表達歷史縱深性真理,而是帶著自身的多重性去映射一個自身透視後的歷史感性:一個內部爭吵不休、相互傾軋、喬裝互謔、抹消重視諸種歷史文本的譯體技藝。
此論述源於兩個欲望:言說與再言說,前者指向翻譯,後者指向再翻譯,可以說,兩者皆是構成所有書寫的「前佔有」。「前佔有」意味著,那些先於此刻話語的語意叢集與其所生產的行動,讓此刻言說傾向於瞄準局部歷史、反對理想意義的書寫展開;亦同時向譜系學的無數轉寫、零碎殘缺的文字把握靠攏。這樣譜系學式的書寫無疑具備了某種「拒絕」性格—拒絕「起源」(Ursprung)的追究—此性格保持了對事件(局部歷史)的敏感性,但不追蹤事件發展的邏輯曲線,它較願意以不同的場景、不同的剪接、不同的旁白、不同的演釋去重新發現事件,這便是「噤聲主體」的言說聲脈與書寫方法,換言之,一種譜系學式的翻譯語體。
拒絕「起源的追究」不僅是此翻譯語體的譜系性格,亦對「翻譯」的主要問題意識。翻譯並不僅是一種異語言的換置,它同時伴隨著發語者的個人脈絡、文化體系與精神結構。當語言從翻譯個體內在向外傳輸的那一刻,便標誌了至少兩套語系的差異與重複。然語言文字永遠是多義且與時境語脈共振的複雜叢集,如同歷史事件,當我們企圖在事件起源中尋求最精確的始然,最同一的邏輯發展,便是「試圖找到『已然是的東西』,找到一個與其自身完全相似的意象的『那個自身』;這就是把所有本應發生的枝節、所有計謀和偽裝當作外在和偶然〔…〕最終,揭示源初的同一性。」[ 註1 ] 然翻譯體並非在追尋那種「已然是的自身」(字義、音準、標準化話語),而是在異種語言之間的偶然縫隙中安身立命,因為他熟知在所有的已然與語義表皮之下之外,永遠有著無法確知、難以精確轉譯的他項參數。如同譜系學者,「如果譜系學者傾聽歷史的聲音,拒絕形而上學的信仰,他會尋獲一切事物背後皆有著『完全不同的某物』:並非永恆的、本質性的秘密,而是事物本身沒有本質性。」[ 註2 ] 無論是說書者、小說家、劇作家或旁白敘事者,如果每一段歷史場景書寫都是歷史事件的現世不在場翻譯,將可把握的證據細節書寫;那麼辯士、口譯者、口傳人便是駐足於現世事件場景的眾多「起源者」,將不可把握的細節把握,以聲音變頻輸出。我們閱讀傾聽到的,是歷史旁白語句,是每一個不連續歷史事件的負像(而非正片)劇場演出。循此語法,「噤聲主體」試著將那些散落的說話者、書寫者、歷史事件等,進行言說與再言說,翻譯與再翻譯,叢集諸種非連續、不穩定的歷史切片,從外部旁白、以影像圖層結構出一紙語言、概念、視像的語體平面,演釋著歷史,或許也擾動了歷史。因此這些叢集所聚合的語言、概念、視像並非單向式邏輯性的直述句法結構,發話者與被書寫者更多的是駐於替換、轉移、渡越、被拒、喬裝、自行決定語法的異聲體,以不同的話語於相異的場景現身。
「十年後戰爭書籍如潮水湧洩般被拋出來,但其中所講述的絕不是人們口傳的那種經驗。」班雅明在〈說故事者〉(The Story teller)中給了我們這樣的警告。根據班雅明,此種「經驗貶值」的原因,來自於現世訊息移動方式的改變。「遠行者必會說故事」意味著身體於現實空間中遊蕩累積的直接輸出,同時也意味著口傳行述因記憶的不準確所可能給出的諸種變異、偶然、無法重複與再繁生,這當然也包括了聽事者自身的差異條件。口傳者為事件的譯體,如同編劇、導演的位置,將人物場景事件剪接演現;聽事者為辯士譯體,如同第三人稱式的編劇、導演,將聽睹的人物場景事件再次擴演流竄。歷史旁白便是此種班雅明式的故事陳述者,或者更精確一點說,它談的不是「故事」,而是「如何敘事」。「故事」傾向於書寫,書寫性的訊息移動有著複本性格,排除變異;「敘事」則向身體經驗靠攏,它揉雜沈積了每一次口傳時的反身性差異,敘事者是他異旁白的譯體。改編重演、記憶重組、口傳變異、複調敘事,敘事譯體提示我們事件直陳與精確翻譯的不可能,同時揭示此不可能所欲豐融繁衍的欲望。
美學與政治視差、翻譯斷裂、對話缺席、(未)出現的預言者、再見劇場等,若語法重組是開展生三成異連鎖辯證的論述路徑,那麼我們是否能把口傳事件生成旁白、以入眾複徑生成場景,藉由翻譯語體重複說著病徵:「我們現在的『現代』是個外來語。」(劉大任語)來生產免疫系統。當亞陶的擬聲詞作為一種既非模仿性語言也非名稱的創生詞,「它將我們重新導引向那個已不再是喊叫卻仍未成為話語」的離散語境,透過書寫文學的複語化、影像化、劇場化,與作品影像的直接翻譯與當下在場,入眾叩問渡越主體、前衛劇場、翻譯文學的現地表達。
Foucault, Michel(1977). Nietzsche, Genealogy, History. In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Selected Essays and Interviews, edited by D.F. Bouchard.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142.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