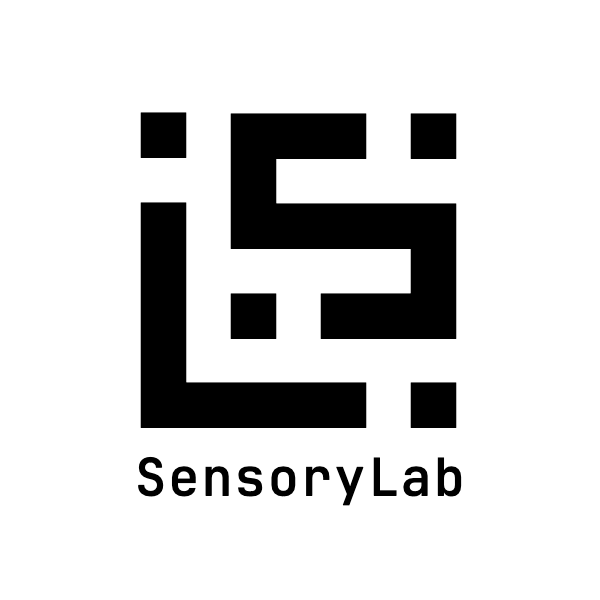日期──2016年3月12日
地點──台中馥漫咖啡
受訪者──鍾喬
訪談人──林欣怡、龔卓軍、羅文岑、郭嘉羚
整理──藝術觀點ACT編輯臺
本文發表於《藝術觀點ACT》,NO.67,2016.07

2016年初台西村村民與差事劇團以《證言劇場》和《女媧變身》二劇在飽受石化汙染的台西村的演出,展現了鍾喬多年來投入民眾劇場研究與實踐所思考的現實事件與劇場的聯結,編輯臺藉由與鍾喬導演的訪談,進一步探究他在歷史、事件、劇場、身體與行動之間的思考脈絡。
「證言」,從動作到行動
林欣怡(以下簡稱「林」)──《證言劇場》是怎麼開始規劃和接觸村民的?又是怎麼命名的?
鍾喬(以下簡稱「鍾」)── 2014年的春天,策劃「南風攝影展:台西村的故事」的自然科學博物館研究員黃旭先生問我要不要去台西村那邊做社區劇場,因「南風」展而認識了攝影師許震唐和鐘聖雄,以及同樣來自台西村的立儀,他們把「南風」的運動層面撐起來,然後是透過他們接觸到村民。2014年我們開始在村子裡工作,我知道對村民來說重點不在於表演,他們有現實的問題,需要有人聽見他們。所以我就安排客家電視台跟他們做深度訪談,然後客家電視台接著又去那邊辦村民開講,這對於村民來說是很大的鼓舞,讓他們覺得自己的現實問題被人家看到、聽到。所以當時就形成白天訪談,晚上排練,這也就成為了「南風攝影展」開幕時的演出。
事實上,從過去參與鹿港反杜邦事件時逐漸建構的經驗,讓我比較深刻地知道,這些底層的環境污染受害者是怎麼看待這些事件,他們的需求是什麼?我們怎樣用文化行動的方式,讓他們能夠成為表現的主體?對我來說,和村民取得一個信任關係的過程,大概就是在找尋一種「對等的視線」,你會一直想要去找一種平等,然而事實的狀態卻並非平等。但有一種可能性是我們應該去做的,就是對等,怎麼樣透過我們的工作去扶持他的主體性,如果你能做到,就有所謂的對等。所以,晚上排練時,我就會趁機告訴他們:「你們大家如果坐下來跟社會大眾說也許有效,我也不敢保證,但是至少你們共同坐下來了,這點很重要,你們不願意的話,就會永遠都在巴望民意代表幫你們發言。」
《證言劇場》的命名,來自我在《人間雜誌》工作時,接觸到由一群日本記者所組成的「不死鳥劇團」(「事実の劇場 劇団不死鳥」由日本記錄作家石飛仁帶領),他們用「報告劇」的方式將日本政府戰後竄改教科書內容中的事實表達出來(1984年花岡事件-中国人強制連行の記録報告劇)。而我去台西村的時候,就想到這種「報告劇」,但是在台西村那個場合是村民共同坐下來,它不只是報告,我認為比較接近村民自己的「證言」。演出的這八位村民是從一開始就比較核心且願意投入的,他們對於這個活動一直不太有自信,我跟立儀說,其實不要再用「運動」去想這件事,就算到時候只有三個觀眾,我們也要做到底啊!在這些活動舉行之前村民很容易被資方或者官方分化,因為他們根本就不曉得怎麼判斷,經過兩天的活動以後,村子裡面的人跟參與演出的萬福伯說:「我們終於知道你們在做什麼,不然以前大家都會說你們就是想要拿錢啊,要補償啊!」從四、五年前立儀和其他團體開始進行反國光石化的活動,整個雲林和彰化,現在應該只剩下我們這個台西村的村長會出來組織反國光石化活動,非常不容易!
羅文岑(以下簡稱「羅」)──《女媧變身》和《證言劇場》兩個劇的先後關係是什麼?
鐘── 是《證言劇場》先發生的。「南風攝影展」繼科博館展出之後,也在寶藏巖以及去台塑門口辦了移動型展覽。2015年初,我帶著差事劇團的團員到台西村,想籌備一場差事劇團版本的的演出,當時我聯想到女媧的神話,魯迅在《故事新編》裡寫女媧的那篇〈補天〉寫得非常生動,一開始形容女媧祂幽幽呼呼地醒來,祂有一點厭世,寫到後來女媧死後躺下來變成豐腴的一片土地,所有的軍隊和以前批評祂的人聚攏到祂的肚皮上去,互相打仗。我覺得這都在指涉中國當時內部搞封建的人物,我想:「這不就是現代世界嗎?」以前是打仗,現在是資本戰爭,女媧一定覺得你們這些人對土地破壞已經讓我覺得無以生存下去。所以就從魯迅這篇〈補天〉開始改編成《女媧變身》這齣劇。
林――您曾提出「從動作到行動」是透過什麼方法從「執行一個動作」到「發動成一個文化行動」?按照這個概念,您認為台西村的「證言劇場」是「行動」,而《女媧變身》是「動作」嗎?
鍾――我想就「動作(act)」和「行動(action)」的差別來說,「動作」是演員刻意要去表現一個角色,要轉換自己去變成另一個人,這是我們對於表演的制式認識;但如果是舞台上的「行動」,便會涵蓋到我們參與社會的公共議題,而不只在表面上和身體上表演別人而已。其實要做一場戲免不了要「act」,但是這些年我覺得「action」比較重要,「action」承載不一樣的方式。譬如《女媧變身》是結合對戲劇有興趣的人,是一起做民眾戲劇很久的夥伴,我們要共同演一齣從現實改編而來的戲劇,所以它基本上是來自戲劇的「美學行動」。但戲劇裡面所涵蓋很多空間的、角色的元素既不必要也無法放在當事人身上,對台西村的人而言,最迫切的是把想要說的話說出來,而我們的工作就是去幫他們找一種方式,我覺得這就是「劇場行動」。

劇場作為暴動的前實踐
林――您的書寫中經常提到貝爾托‧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 1898-1956)、奧古斯都‧波瓦(Augusto Boal, 1931-)和櫻井大造(Sakurai Daizo),能不能談談他們給予您的影響?
鍾――八○年代初期,我念文化戲劇研究所時,受教於姚一葦老師(1922-1997),那時候在劇場美學的論述中接觸到布萊希特和盧卡奇(Lukács György,1885-1971),但他們和德共(德國共產黨)、蘇共(蘇聯共產黨)的關係,在台灣未解嚴的時空下很少人會刻意去談,不過因為當時我在《夏潮雜誌》工作而接觸了左翼、馬克斯,所以那時候自己會去像桂林書局地下室這樣的地方買布萊希特、盧卡奇和馬克斯主義的英文書來讀。儘管當時都是透過劇本認識布萊希特的《四川好人》(1943)、《高加索灰闌記》(1944),然而他提出的「陌生化效果」影響了我對劇場和現實關係的思考。
而波瓦是把布萊希特實現出來的人。在布萊希特的劇場裡,希望觀眾回去以後繼續思考戲劇帶給你「對於現實的思考」;但對於波瓦而言,觀眾也可以上台來,這就變成論壇劇場(forum theatre)的開始,等於是把布萊希特往前推一步。九○年初期,我從菲律賓亞洲民眾文化協會創辦人艾爾‧山多士(Al Santos, 1954-)那裡拿到波瓦寫的《被壓迫者劇場》(Theater of the Opressed),這本七○年代的書早已被第三世界國家小劇場的人讀了二十幾年。 這意味著臺灣經過五○年代白色恐怖時期對左翼的肅清與嚴密控管,已經不是「外在」而已,而是已經「內化」到生活、身體裡面的任何一種價值觀,因此我們根本就不會知道波瓦以及第三世界。更由於毛澤東在長征的期間透過「活報劇」向被壓迫的農民宣傳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思想,所以國民黨到了臺灣,對於「戲劇」控制得特別嚴格。與美國的反越戰以及全世界女性主義的運動盛行同一個時期,我在菲律賓的這些朋友在七○年代時,已經用這種方式去搞他們的劇場運動,然而在七○年代的台灣,整個左翼運動卻是沒有聲音的。
1988年陳映真找我回去《人間雜誌》當主編,那時候恰巧藍博洲開始寫《幌馬車之歌》。當《人間雜誌》刊出《幌馬車之歌》時,陳映真說過藍博洲這個作品對於將來發掘白色恐怖會是一個關鍵。一晃眼二十幾年過去了,我覺得白色恐怖的事情,應該要重新面對世代變化,而且現在全球化以後這麼的貧富不均,這是左翼應該可以重新現身的時候,但如果青年一輩的人都沒有任何的思想準備,那要怎麼面對?所以4月份差事劇團在台北演出的《幌馬車練習曲》這齣戲就是由我來製作,然後找來林靖傑導演,用他的電影美學和更年輕的演員從尋找左翼開始對話。
林──您的小說和劇本其實在一條生產的路徑上,先聚集歷史、文學、藝術,最後用身體結構出來成為劇場,那麼,您認為劇場之後,可以是什麼?
鍾──暴動。事實上七○年代的西方的戲劇大師彼得.布魯克(Peter Brook, 1925-),本來也相信這個,但到了2000年以後,他們事實上已經不相信以前所做的一些事情,他們已經和大劇場做連結了,也變成大師了,我相信變成大師就不太適合暴動了。
龔卓軍(以下簡稱龔)──青年世代對都市空間、對社會結構的重新想像,本來應該是透過劇場的實踐而變成一個暴動。可是台灣在五○到六○年代有一個很大的空缺,完全缺乏現代化經驗這一塊,並沒有重新連結農民、工人的力量,把這種力量集結在都市的空間裡面。反而現在透過報告劇或證言劇場,都一直指向這個空缺,重新去做這個連結,所以您剛說「暴動」我覺得是個關鍵字。向您提到的菲律賓在六○、七○年代已經經歷過那一段,後來八○年代到柏林圍牆倒塌這段過程,不管是東歐也好、南美洲也好,就像波瓦經歷的狀況,其實是劇場在作用,這些運動或革命裡,劇場的力量是非常強的,台灣這邊卻完全沒辦法展現。
對寫作領域的問題來說,如果完全往實驗那邊推的時候,是真的可以置外於臺灣歷史的發展,而且學院阻隔了寫作本身納入到歷史處境跟內涵的必要性。但是,事實上延續現代主義的或是鄉土文學論戰這個脈絡接下來的,還有一大片的問題沒有處理過,並不是像馬奎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1927-2014)能在自己的南美洲運動脈絡中直接跳到魔幻寫實去解決的那種問題,但是我們從大學到研究生學習的過程,的確都沒辦法碰到臺灣自己的歷史,純粹是翻譯外來的文學,學習技法,而不曾提到左翼運動的歷史。
鐘──台灣的白色恐怖就是總體的斷裂。在1968年的時候,臺灣人是完全不能夠發出聲音的,但第三世界早就已經如火如荼在進行各種運動與革命,我們落後第三世界二十年,我竟然變成第一個把波瓦那本書拿到台灣劇場的人,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尋找亞洲的身體
鍾――從1998年我引介櫻井大造的帳篷劇「野戰之月」在台北重新橋下演出《出核害記》以來,慢慢地理解到櫻井是怎麼樣在他自己的實踐上面看待他的思想,這件事情對我有很大的啟發。最早我在1995年在菲律賓的馬尼拉遇上櫻井,日本的「黑帳篷劇團」(由佐藤信於1968年成立)一直和菲律賓教育劇團有密切來往,當時我和櫻井比手劃腳,有一句沒一句地聊天、一起看戲劇節。在馬尼拉的這段經歷,對我來說也是我在民眾戲劇的啟蒙,譬如透過一個「題材」讓農民、漁民發現自己的問題。有意思的是,櫻井站在一個反啟蒙的角度,所以表演論述是永遠沒辦法碰觸到帳篷劇的核心。六○年代戰後的日本,已經在整個社會與戲劇界的共識之下放棄寫實戲劇,他們認為「表現」已經不再是寫實的,所以採用很多隱喻和哲學就成為櫻井的風格。
帳篷劇的開始和安保鬥爭有很大的關聯,那些退到學校的學生為了反抗警察的包圍而建立了自己的堡壘,從這裡轉為帳篷劇的概念,這個堡壘也就是社會底層被迫害、被壓迫者唯一的生存之地,但堡壘是可以移動的,先去佔有一個地方,做完一件事後還給那個地方清白。帳篷劇就是在建構一種共同勞動、共同表演的過程。從搭帳篷開始,就是在創作他們和這個社會的關係,搭起帳篷就像設了一個可以在裡面生存和表演的反抗世界的堡壘。櫻井常說,帳篷就像皮膚一樣,隨時感受得到外在世界,但是外面的世界會不斷傳來聲音、干擾,所以並不是處在安全的狀態下表演。這就是櫻井對現代世界的認識,同時也是現代社會的一個狀態。
林──您曾在〈每個人的身體裡都有第三世界〉中提到透過「視線」從世界結構回到我們身體裡面去找尋自己內在的第三世界、亞洲的身體,這種亞洲的身體或者我們在劇場裡表現出來的的身體,是否最終可能形成的一套被符號化方法,而成為大家已經熟悉的那種「亞洲的身體」?
鐘──我在八○年代的時候,參與人間雜誌、自己寫詩,一定程度地了解到臺灣文學、戲劇 、現實主義這些事情,然後參與社會運動後就重新把文學或是戲劇的表現怎樣和現實產生關聯找回來。劇場就會讓人很快地想起身體這件事,這個身體和世界觀其實是有關聯的。其實我們長久以來透過劇場來表現的身體的世界觀是西方的、從希臘悲劇以降的這些橫向移植和模仿而來的東西。九○年代我參加「亞洲的吶喊」開始對於亞洲的身體這件事情進行反思,當時看到菲律賓的導演山多士在亞洲尋找每一個七○年代的民眾戲劇,從東南亞到南亞再到日本,和這些人共同作一個以身體出發的戲。在那個時候我也閱讀到薩伊德(Edward Wadie Said, 1935-2003)所談的東方主義,將自己的傳統變成取悅歐洲的異國情調,以及法蘭茲.法農(Frantz Fanon, 1925-1961)所說民眾的事情應該是讓傳統有一個新的波動,它和現實能夠產生一種激盪而不會變成異國情調。所以我認為亞州的身體應該再回到第三世界,不是要揚棄傳統,而是回到一種人的世界觀,不是「美─善─真」,而是以「真─善─美」的順序,重新去看待第三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