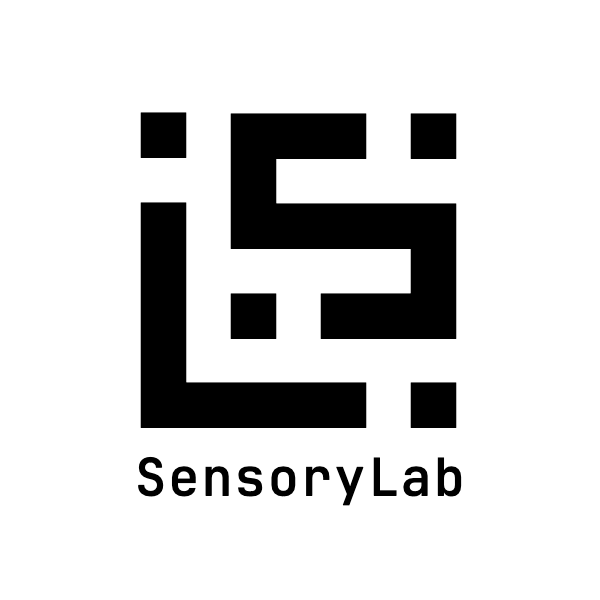2017 [ 研討會論文 ]
鯤言:
閾限空間中的聲響
Voice-Over of History:
From Jokaisen-Kitan to the Subject in Transit
━━━━━━━━━ 林欣怡
// 本文節錄自〈Voice-Over of History: From Jokaisen-Kitan to the Subject in Transit〉
// 發表於 MediAsia 2017: The Asian Conference on Media, Communication & Film 2017,2017.10.27-29, Kobe, Japan